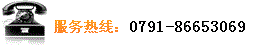回望2015年,以增長中樞下降、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緩為核心特征的全球經(jīng)濟(jì)新常態(tài)進(jìn)一步強(qiáng)化。從成因看,某種程度上,全球化放緩是前兩個新常態(tài)的衍生結(jié)果,并加固了前兩種新常態(tài)。由此,各國對復(fù)蘇利益的爭奪更趨激烈,個體理性導(dǎo)致集體非理性,全球化推進(jìn)缺乏統(tǒng)一行動。全球化放緩又反過來對全要素生產(chǎn)率形成沖擊,造成進(jìn)一步的增長拖累;而由于新興市場融入全球化的邊際收益高于發(fā)達(dá)國家,全球化放緩又導(dǎo)致了多元化退潮的進(jìn)一步深化。
2015年行至尾聲,在廣泛分析各類政經(jīng)事件和宏觀數(shù)據(jù)的基礎(chǔ)上,筆者發(fā)現(xiàn),以增長中樞下降、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緩為核心特征的全球經(jīng)濟(jì)新常態(tài)進(jìn)一步強(qiáng)化。新常態(tài)包含兩層含義:一是“新”,全球經(jīng)濟(jì)外在的演化趨勢和內(nèi)在的運(yùn)行機(jī)理都呈現(xiàn)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,舊秩序被打破,新秩序“將立未立”。在秩序轉(zhuǎn)變過程中,不確定性廣泛存在,增長規(guī)律、市場法則、變量關(guān)系、預(yù)期機(jī)制和博弈均衡都不斷發(fā)生著經(jīng)典理論和傳統(tǒng)經(jīng)驗(yàn)難以解釋的變化,地緣政治動蕩頻繁,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。二是“常”,全球經(jīng)濟(jì)運(yùn)行發(fā)生超預(yù)期的變化,這并不是短期現(xiàn)象,而是不斷被確認(rèn)的中長期態(tài)勢。
市場永遠(yuǎn)是對的,需要修正的是預(yù)期。放下對舊秩序的執(zhí)念,認(rèn)識新常態(tài)、理解新常態(tài)、適應(yīng)新常態(tài),是政策決策者、投資者和消費(fèi)者“順勢而為”的前提。
新常態(tài)特征一是增長中樞下移。全球經(jīng)濟(jì)正在經(jīng)歷一段失落時光,復(fù)蘇力度羸弱,表現(xiàn)在三方面:一是弱于趨勢水平。根據(jù)國際貨幣基金組織(IMF)10月的預(yù)測,2015年全球經(jīng)濟(jì)有望實(shí)現(xiàn)3.12%的增長,增速較2014年下降0.3個百分點(diǎn),弱于1980年至2014年3.5%的歷史平均水平,及2008年至2014年3.28%的危機(jī)平均水平。IMF預(yù)測,2016年全球經(jīng)濟(jì)增速將回升至3.56%,鑒于IMF一直表現(xiàn)出明顯“過于樂觀”的傾向,筆者對2016年全球經(jīng)濟(jì)能否回到趨勢水平以上充滿疑慮。
二是弱于預(yù)期水平。全球經(jīng)濟(jì)復(fù)蘇一段時間以來的表現(xiàn)始終令人失望。在10月的預(yù)期更新中,IMF將2015年和2016年全球經(jīng)濟(jì)增長預(yù)期較7月均下調(diào)了0.2個百分點(diǎn);還將2015年發(fā)達(dá)國家和新興市場經(jīng)濟(jì)增長預(yù)期較7月分別下調(diào)了0.1和0.2個百分點(diǎn),將2016年兩者的經(jīng)濟(jì)增長預(yù)期也較7月均下調(diào)了0.2個百分點(diǎn)。
三是覆巢之下難有完卵。筆者利用更新后的WEO數(shù)據(jù)庫測算,在IMF有統(tǒng)計(jì)數(shù)據(jù)的188個經(jīng)濟(jì)體中,2015年,有115個經(jīng)濟(jì)體經(jīng)濟(jì)增長預(yù)估值低于其1980年至2014年的歷史平均水平,有107個經(jīng)濟(jì)體增長預(yù)估值低于2014年;全部188個經(jīng)濟(jì)體的增長預(yù)估值低于歷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達(dá)1.07個百分點(diǎn);而即便根據(jù)IMF習(xí)慣性“過于樂觀”的預(yù)測,2016年全球188個經(jīng)濟(jì)體經(jīng)濟(jì)增速還將低于其歷史水平平均0.05個百分點(diǎn)。
IMF將全球經(jīng)濟(jì)復(fù)蘇羸弱的短期原因歸結(jié)為總需求疲軟、政策乏力、大宗商品價格下跌、前期信貸過快增長的負(fù)面效應(yīng)和政治動蕩。筆者認(rèn)為,弱復(fù)蘇的根本原因是增長中樞下移成為新常態(tài)。
新常態(tài)特征二是多元化退潮。以2010年為分界點(diǎn),全球經(jīng)濟(jì)多元化從漲潮變?yōu)橥顺保?ldquo;發(fā)達(dá)國家向下、新興市場向上”的趨勢被“發(fā)達(dá)國家向上、新興市場向下”的趨勢所取代。多元化潮起潮落的關(guān)鍵指標(biāo),是新興市場經(jīng)濟(jì)增速領(lǐng)先發(fā)達(dá)國家的剪刀差。2000年,這一剪刀差為1.77個百分點(diǎn);隨后一路上升,2009年達(dá)到6.55個百分點(diǎn)的峰值;2010年起逐漸下降,2014年降至2.79個百分點(diǎn);據(jù)IMF10月最新預(yù)測,2015年新興市場和發(fā)達(dá)國家經(jīng)濟(jì)增速分別為3.97%和1.98%,剪刀差降至1.99個百分點(diǎn),創(chuàng)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,危機(jī)以來首次低于1980年至2014年2.18%的歷史平均水平;2016年,IMF預(yù)測新興市場和發(fā)達(dá)國家將實(shí)現(xiàn)4.52%和2.23%的經(jīng)濟(jì)增長,剪刀差有望小幅回升至2.29個百分點(diǎn),即便如此,這一水平還將顯著低于2014年。
數(shù)據(jù)表明,2010年以來,多元化退潮漸成新常態(tài)。2015年,退潮進(jìn)入“高潮”,不僅新興市場和發(fā)達(dá)國家經(jīng)濟(jì)增速剪刀差創(chuàng)15年新低。兩者的邊際變化也呈現(xiàn)出大范圍此消彼長的態(tài)勢:根據(jù)IMF的預(yù)測,2015年,發(fā)達(dá)國家經(jīng)濟(jì)增速較2014年提升0.2個百分點(diǎn),新興市場經(jīng)濟(jì)增速卻是較2014年下降0.6個百分點(diǎn);美國、歐元區(qū)和日本經(jīng)濟(jì)增速分別較2014年提升0.2、0.6和0.7個百分點(diǎn),俄羅斯、中國、巴西和南非經(jīng)濟(jì)增速卻分別較2014年下降4.4、0.5、3.1和0.1個百分點(diǎn),印度經(jīng)濟(jì)增速持平。
根據(jù)2014年哈佛大學(xué)CArmenM.Reinhart和KennethS.Rogoff一項(xiàng)研究,發(fā)達(dá)國家走出全球性危機(jī)一般需要7年,新興市場則需要13年。這也就是說,從歷史角度看,此消彼長的多元化退潮或許會持續(xù)至少6年。
新常態(tài)特征三是全球化放緩。作為一種內(nèi)生趨勢,全球化很難出現(xiàn)真正意義上的倒退,但全球化放緩卻漸成新常態(tài)。全球化放緩表現(xiàn)為保護(hù)主義抬頭、地緣政治動蕩、要素流動滯澀、以鄰為壑氛圍加重等多個層面,最重要的表征是國際貿(mào)易增速放緩。看長期數(shù)據(jù),全球化放緩始自2012年。1980年至2014年,全球貿(mào)易平均增速為5.43%;2010和2011年,全球貿(mào)易增速高達(dá)12.52%和6.67%;2012年驟降至2.91%,隨后幾年也始終低于歷史均速。IMF預(yù)測,2015年,全球貿(mào)易增速為3.18%,2016年有望小幅回升至4.08%,但依舊低于歷史平均增速。發(fā)達(dá)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出口情況基本和全球趨勢類似。全球化放緩的態(tài)勢自2014年以來快速惡化。地緣政治動蕩加劇,烏克蘭危機(jī)、ISIS恐怖主義和希臘退歐危機(jī)相繼引致市場恐慌;國際政策博弈逐漸趨向“囚徒困境”,競爭性貶值不斷加碼,國際金融秩序受到巨大沖擊;國際貿(mào)易則進(jìn)一步放緩。
從成因看,某種程度上,全球化放緩是前兩個新常態(tài)的衍生結(jié)果,并加固了前兩種新常態(tài),形成一種新常態(tài)內(nèi)部惡性循環(huán)、整體自我固化的態(tài)勢。全球經(jīng)濟(jì)增長中樞下降和多元化退潮背景下,各國對復(fù)蘇利益的爭奪更趨激烈,個體理性導(dǎo)致集體非理性,全球化推進(jìn)缺乏統(tǒng)一行動。全球化放緩又反過來對全要素生產(chǎn)率形成沖擊,造成進(jìn)一步的增長拖累;而由于新興市場融入全球化的邊際收益高于發(fā)達(dá)國家,全球化放緩又導(dǎo)致了多元化退潮的進(jìn)一步深化。